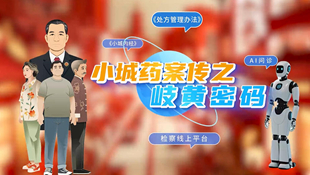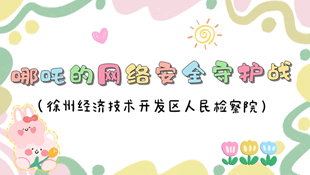日本昭和四十六年六月,东京蒲田发生一起杀人案。被害者为正直善良的退职警察三木,被人用钝器击伤头部死亡,凶手又制造出被火车轧死的假象。一个好人,在异乡死于非命,是谁,为何要置其于死地?改编自松本清张同名小说的电影《砂之器》,借助两位警官的缜密取证调查还原了一位人生赢家经历冷暖爬上顶峰,为了掩盖曾经的出身及篡改身份的秘密最终丧失人性的悲剧。
影片开始,一个男孩孤独地在沙滩上用沙子堆砌出一个个精美的容器,海浪袭来,瞬间坍塌消失……编导借此暗喻主人公最终的命运走向。
和贺英良(秀夫)是公众眼中的天才音乐家,正着手创作钢琴协奏曲《宿命》,他还有个身份是前大藏大臣的准女婿。所有光鲜与掌声,都无法遮掩其幼年的痛苦。当年由于父亲千代吉患有麻风病,六岁的秀夫与父亲开始流浪。在世人唾弃时,只有“活菩萨”警察三木收留了他,并将其父送去治疗。后来秀夫离开三木,借机修改了身份,并通过努力成为著名音乐家,前程似锦。偏巧,多年后外出旅游的三木看到英良与大藏大臣一家的合影,当即找到他,执着地拉他去疗养院见见已是风烛残年的亲生父亲千代吉,可英良惧怕暴露过去,于是残忍地杀死了养父三木。
有小说珠玉在前,改编者自然要用足电影语言,删除旁枝末节更好地叙事达意。在保留原著基本情节基础上,影片对故事脉络作出微调,把时间调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将和贺英良“美化”为令人同情的悲情角色。
悲惨经历对谁都刻骨铭心,有人要牢记,更有人想深埋,如同内心的黑洞,无法凝视。那些曾经帮助过、深谙自己的人,同时也是一条瞬间能把自己拉回用尽一切手段全力隔断过去的纽带,对贫穷、屈辱的绝望,企图彻底切断关联,于是启动了人性的冷酷与决绝。作品在离奇情节的抽丝剥茧外,加入社会写实内容和犯罪动机分析,令主题更加突出。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恩将仇报的故事,不仅仅讲述一段令人唏嘘的个人奋斗、挣扎和毁灭过程,更因为其特殊的历史隐喻,成为日本国民共有的战前经历与集体记忆的象征性写照,《砂之器》上映后收获一致好评,获得1974年度《电影旬报》十佳奖第二名,仅次于《望乡》。松本清张本人也认为该片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改编,甚至超过了原著。
在影片最后二十分钟,创作者高超地运用钢琴协奏《宿命》的音乐烘托主题,仿佛是无数生命经历悲苦后发出的一声声呐喊,通过镜头闪回方式,展现三个平行场景:警官通过蛛丝马迹讲述案件背后的隐秘故事;聚光灯下,和贺英良深情弹奏《宿命》;时空交错、四季轮回的日本列岛,千代吉与秀夫衣衫褴褛,尊严被践踏时,却饱含父子温情……那些深入骨髓的寒冷与疼痛,以具体的、鲜明的音乐元素迸发出来,升华了情感与现实的激烈碰撞。
悲剧,终无法幸免。此时主人公的心中,该是有悔恨与愧疚吧,否则他的眼中怎么会有泪光?“今西,其实和贺是想见到父亲的吧?”“当然是的,他正和父亲相会,他只能在音乐里和父亲相会。”那一场演出,不是宿命,只是告别。
主人公所遭受的境遇,甚至最后由于极端利己主义而犯罪归结为“宿命”,是该片“短板”,背离了松本清张社会派推理小说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
探讨人性、人情、人伦,同年代另一部日本影片《人证》同样获得高分评价。八杉恭子为了维护地位和名誉,亲手杀死从美国来寻母的混血儿子及知情人,逃亡路上的另一儿子因拒捕遭杀。最终失去一切的她,把儿子的草帽扔向山谷,跳下山崖……片尾,音乐同样给影片注入灵魂。
“妈妈,你可曾记得你送给我的那顶草帽,很久以前我把它弄丢了。那草帽飘摇着坠入了浓雾弥漫的山谷,妈妈那草帽是我唯一珍爱的东西。但我们失去了它,再也找不回来了。就像,你给我的生命。”此刻,象征母子羁绊的草帽在空中飘荡,伴随悲怆的歌声,主人公背影随之消失,令观众最终体味影片深藏的寓意。
当年,作为第一批引入内地的日本影片,《人证》中来自诗人西条八十的主题曲《草帽歌》经由日美混血歌手乔山中传遍大江南北,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与《宿命》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没有了西条八十,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人证》的魅力或许都会减半。
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恶魔,只是没有被唤醒。时光流逝,那些充满屈辱、无助的经历,那些不惜以生命阻断的前尘往事,可能仅仅因为一个偶然被打开……竭力埋葬过去,不惜制造罪恶。主人公的命运沉浮背后,不仅仅是个体悲剧,更是时代之耻。
人们常说,往事会被时间冲得越来越远。但有些往事在记忆中会越发沉重。爬上人生顶峰,背后有多少悲伤,又有多少肮脏,无法考量。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历史留下的破败与伤痛却在所有人心中无法删除,落到每个人的身上都是一块巨石。如今,重看这部电影仍然令人唏嘘不已。
砂做的器皿只是表面光鲜,但毫无根基,一旦潮水袭来便化为乌有。或许,三木就是那波潮水……若没有现世安稳,悲剧不会就此结束。俯瞰人间烟火,长乐永康应是所有年代,所有生命的梦寐以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