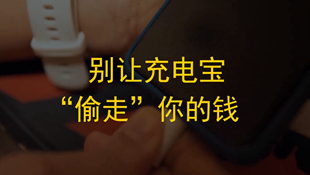思想是文学批评的灵魂,是普罗米修斯盗来的火,也是文学批评赖以存续下去并诱使一代又一代杰出头脑投身其中的理由
文学批评大概是最勇于自我革新的文类。一段时间以来,这一文类将革新重点放在“文体”上。批评家们热衷于谈论“文章之道”,试图将文学批评从学术阵营拉到文学阵营中来。这固然反映了文学批评对于读者日渐减少的焦虑——仿佛写得好看一些,就能争取更多的注意力,然而这也反映了文学批评超越时间限制、获得永恒名声的企望。因为,倘若没有风格,批评断然是不可能成为文学而只是文学的附属品,因而无法战胜时间。在我刚刚开始学习批评写作的时候,就接受了诸如此类的教诲。如果还不能写得好一点,就写得漂亮一点吧。我叹服于别林斯基的气盛言宜,激动于桑塔格的锐利精致,感佩于李健吾的才华横溢。对于我来说,他们都显示了“文章”的典范,展示了文学批评之美是多么迷人。
时至今日,在漫长试笔和不断试错之后,我终于认识到,“写得好”与“写得漂亮”之间,还是有着不言自明的距离。倘若没有深邃思想,所有“漂亮”都不过是虚妄。就好像好看的皮囊与有趣的灵魂并不一定永远合体,如果让我选择,我肯定会选择有趣的灵魂。无法想象,别林斯基、桑塔格、李健吾们只擅长遣词造句,只提供空洞无物的“美文”,他们大约无法穿越时间和空间,投递到我们的文学生活中来。是的,思想是文学批评的盐,是灵魂,是普罗米修斯盗来的火,也是文学批评赖以存续下去并诱使一代又一代杰出头脑投身其中的理由。
那么,思想又是什么呢?思想是对文学作为一门艺术的不断重新定义与发现。身为一个文学批评家,他必须时刻警觉,同时代文学在技艺上有哪些精进,又有哪些新的开创,这一风格与传统有怎样的关系,对未来写作又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文学批评家所必有的意识,也是他必须要在文章和谈话中反复回答的问题。思想还包括认识生活的能力,辨别现实生活与文学世界的关联与差别的能力以及将知识、情感与智慧结合在一起的能力。由是,文学批评摆脱对他人文本的依附地位,获得了与他所评论的对象携手前行的资格,共同在这广袤的人世间探险,共同探究人类生活新的可能。
接下来需要追问的是,思想从何而来?思想需要广博的知识,需要披荆斩棘认识生活的勇气和能力,也需要理解言词的智慧,特别是,它需要理论视野。一度,艰涩理论让文学批评的读者望而生畏,于是,一些批评家将理论视为批评的敌人,认为庞杂的中外文艺理论与当代中国文学“水土不服”,滥用理论使得中国文学成为理论家跑马圈地的训练营。滥用固然是错误的,但如果完全放弃理论训练、丢掉理论透镜,文学批评可能沦为仅仅抒发个人情感的读后感。
因此,有必要重新定义:批评应该作为写作而存在。这意味着,我们在关注批评最后呈现的那个成型“作品”同时,还应注意完成这一“作品”的过程。理想中的文学批评家,应该对阅读怀着常人难以企及的热忱。各种各样的书包围着他,他不知疲倦、专心致志地阅读,并不断为这个世界引入新的意义。桑塔格有一篇文章就叫做《作为阅读的写作》,大概可以用来形容批评家。桑塔格说,“写作即是以一种特别的强度和专注来训练阅读。你写作,是为了阅读你写下的东西,看它好不好”。批评的冲动来源于,那些从阅读中获得的东西促进了你的自我教导与心智成长,你愿意将之与别人分享,邀请他人一起分享生活的意义。
很多年前,当我读到美国文学批评家斯坦纳的一番话时,曾感到前途黯淡无光。他说,“如果能当作家,谁会做批评家?如果能焊接一寸《卡拉马佐夫兄弟》,谁会对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复敲打最敏锐的洞见?如果能塑造《虹》中迸发的自由生命,谁会跑去议论劳伦斯的心智平衡?……如果能赋诗传唱,如果能从自己有限人生中取材并铸就不朽小说,创造永恒形象,谁会选择作文学批评?”现在,在将自己的有限人生贡献给了批评之后,我却获得了某种意义。如果将“创造”视为文学批评的内核,那么,文学所允诺给我们的真与美,都将在批评中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