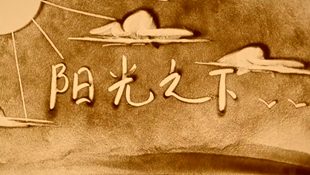此文较多用到英语,放心,我会翻译成汉语,看起来虽不如纯汉语干净利落,但能看懂。
我走在美国洛杉玑街头,去参加南加州影视协会颁发金环奖的活动。此次金环奖受奖者有中国的张艺谋等文化名人,美有关部门邀请中国记者参加。说了,我走在洛杉玑街头,走向颁奖的酒店,一个老外——错了,此地我才算“老外”——在马路另一边追着问我:Japanese(日本人)?
自我打量,短发,红风衣,长条真丝围巾,灰裤子,白皮鞋,怎么就成日本人了?懒得理他,自顾向前走。那人不肯罢休,“日本人?日本人?”马路对面一个劲问。我拐弯后大声说“NO!”没来得及说出“CHINA”,看不见他人了。
那是2002年12月的事,16年前我第一次访美遇到的一件小事。那时美国还没开放成中国的旅游目的地国,去的中国人不多。记得我在一家台湾人开的餐馆就餐,台湾大厨边颠勺边喜滋滋地说,“还是共产党好,给我们送来生意做,有钱赚。”
两年后的2004年五一黄金周,我跟团赴法旅游(2000年跟着中国记协代表团访问非洲途经法国),感觉比第一次有很大不同。
首先,法国航空公司飞机上有了英、法、中三种语言菜单,午晚餐供应极为丰富。现抄录如下:
午餐:虾仁海鲜派、腓力猪排佐龙蒿酱配豌豆及里昂洋葱马铃薯,或蚝油牛肉配中式蔬菜及米饭、干酪、新鲜水果、杏子馅饼、咖啡及茶。
晚餐:螯虾色拉、香烤牛柳火腿及法式巴门特色拉、干酪、鹅莓乳酪蛋糕、咖啡及茶。
虽然游客搞不明白腓力猪排与别的猪排有何不同,巴门特色拉是哪方神圣,但毕竟感觉到一份实实在在的服务,吃得既爽口又开心。
客人到巴黎入住酒店电梯间里有中文告示:限乘6人,不走,不要按灯,下人。生硬一点,意思语法没什么不对。
酒店餐厅早餐供应有了中文标出的“热水”和“热奶”。只是店家低估了中国人水漫金山般的热水用量。
卢浮宫博物馆有了中文地图和画册;船游塞纳河广播里有中文解说,不是带港台口音的中文,是标准的普通话;埃菲尔铁塔显示屏打出中文的欢迎词。巴黎最大商场老福爷,中文在这里简直是花枝招摇,所向披靡。
纪念品区、礼品区干脆雇佣中国导购,小姑娘举着各色香水瓶冲着不论老幼丑俊中国女士一顿狂喷。
那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客人赴欧赴法旅游的大年。
之后10年,欧美亚澳,我去的洲与国不少,当然去的都是该洲的热门国家。大部分跟团,没有人再用“日本人”聒噪你。
2013年春天,我跟团去了国人去的不多的北非国家摩洛哥。
那天参观位于摩洛哥经济首都卡萨布兰卡的哈桑二世清真寺。清真寺高大,奢华,现代感十足,值得专文描述。我从半地下阔大潮闷洗浴厅走出来,走到大西洋华丽丽的阳光下,迎面一位着职业装丝巾包头的女士向我发问:Japanese(日本人)?
怎么一朝回到10年前?我果断答:NO。
Korean(韩国)?
我答:NO!CHINA(不是,是中国)!
她不撞南墙不停步,继续:Hongkong(香港)?
我又恼又烦!大声回答:BEIJING,BEIJING。
她听懂了,敛容正色,出口是中文:你好!
刚想发火的我只有和颜悦色道:你好!
我想,这次对中国人北京人的辨识过程,丝巾包头女士会牢记在心。
第七次赴欧,决定弥补未去过的“俩牙(葡萄牙和西班牙)”,我深刻感受当地人尤其小商小贩对中国人的辨识能力有了突飞猛进。
花街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中央大道,全名兰布琅花街,街的一头由通向地中海的哥伦布广场起,另一头至伽泰罗尼亚广场。欧洲国家广场都不大(比较天安门广场),初始作用是方便人群聚集办事。一般广场周围有市政、司法、宗教、交易场所,西班牙还有地方特色的斗牛场。兰布琅花街是一处知名旅游景点,中间步行,两旁机动车道。除了主街,还有毛细血管样岔道。
花街,当然有鲜花,也有我和妹妹爱买的冰箱贴和明信片。客人朝有心仪货品的店走去,扑面一句“打折”,什么?打折打折,四声准,意思准,原来是吾国语言“打折”,令人无比惊喜。“打折”是个稍有些复杂的词语,“打”已非原有打人之动作,有点像流变后“打车”的“打”。谁教给小店伙计用这枚汉语招呼中国客人——排除韩国日本人——精准而给力。
“打折”小伙引导客人走进小屋,搬出一张纸板,上写1=2C,3=5C。意思是客人挑中的冰箱贴,买一只2欧元,买三只5欧元,这就是“打折”。
再多打点呗!妹妹的话,小伙听不明白,听不明白不妨碍满脸带笑。交易完成后,小伙像是感谢又抛出几枚汉语:饺子,好吃,漂亮。不知说他货品漂亮,客人漂亮,还是买卖做得漂亮。总之搭送几句汉语,哄客人开心他也开心。
2017年,我去了早些年走马看花般游欧洲15天10国中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馆有了中文语音讲解,运河游船上中文语音讲解不仅普通话,还有粤语,我和成千上万到此一游的中国人早就见怪不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