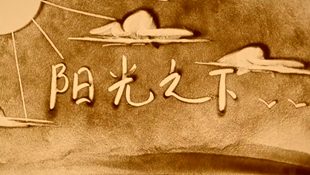月是故乡明,歌是家乡甜。
近段时间,不知何故,我的梦里经常出现家乡的秧歌。
春夏之交,还没等布谷鸟催工,家乡人就为一年的生活大计忙活开了。说是大计,是因为家乡人明白,大米虽不高产但珍贵,比玉米洋芋稀缺,稀缺得平素只在包谷饭里掺少许大米,或是逢年过节才吃米饭。
家乡地处滇东偏北,典型的山地多,平地少,田就更少了。土地承包到户那会儿,还有些高田,也叫雷响田。顾名思义,雷响田纯粹靠天吃饭,谷雨节气一到,家乡的农人们翘首盼雨。终于盼到雨,还未等雷雨过,家乡人披上蓑衣拿起锄头,争先恐后跑向高田,有挡坝的,有放水的,有犁田的,有唱秧歌的。何三大爷的秧歌唱得最响亮,最绵长,在我看来,赛过作家刘震云笔下《一句顶一万句》中的罗长礼。
即便到了夜里,家乡人仍不肯散去,要等田水放满才回。夜幕下,三两处火把,五六声蛙鸣,七八个火星点。往后,火把隐灭了,只有寥寥的火星合着蛙鸣的节奏忽暗忽明。何三大爷通过依稀的火星判断出:哪家的老汉在抽旱烟卷,哪家的老汉在打盹儿,或是秧田水放满回家了。何三大爷咕咚咕咚喝了几口水,清了清嗓子:“夜半三更哟,饿得慌,夜半三更哟,放田水……”这时,抽烟的,打盹儿的,该放口子的放口子,该理水沟的理水沟。何三大爷家的田在最里头,等放满别家的才轮到他家的。后来,我方明白何三大爷的秧歌唱功一方面来自天赋,一方面来自后天的积累,或者说某种潜能在一定条件下得以薄发。
放上田水,紧接着靶田、施肥、平整,一切就绪,就待插秧。待插的秧苗何时拔起有讲究的,秧苗不宜过长,也不宜头天晚上拔起,否则,拔起后的秧苗,换苗时过程长,影响秧苗的长势,进而影响稻谷收成,用满大爷的话讲,就是先天不足。
踏入立夏,就踏上插秧的节奏。三更过后,满大爷的秧歌响起:栽秧要趁早,满前栽是饱满,满后栽就半满。满大爷本姓何,因他小满日出生,又因他的小满秧歌,大家都叫他“满大爷”。满大爷的秧歌比布谷鸟管用,再懒的庄稼汉一听“满后半满”都会一骨碌爬起来,因为饿怕了。家乡人忙着下田拔秧,秧苗拔起,如何清洗根上的淤泥?是将秧苗击水,击水声、青蛙的咕咚声、蟋蟀的蛐蛐声组合成乡村音乐,这何尝不是一种秧歌?
秧苗拔回,“出阁”之前,还有道工序,要把掺夹在秧苗里的“败子”挑拣出来。我问母亲,都是一个色怎么找?母亲说,“败子”就是小米,脚小腰细,它在里头,会影响稻子的产量。我又问,既然它是小米,跟大米是同类,干嘛要拣出去?母亲说,小米是国外引进来的,因产量低养活不了这么多中国人,先祖改良品种,研究出大米,小米没有剔除干净,所以我们还要筛选,把小米拣掉。
秧苗用稻草绳捆好,由不善插秧的小伙送到田里,插秧的主要是手脚麻利的姑娘。姑娘们手起秧落,游刃有余,整齐划一,这齐整的节奏一般由最左端的姑娘带起,姑娘一边插秧,一边哼着秧歌:哎—呃,栽秧嘞,眼要勤手要快,栽秧嘞,就像穿针引线,心要灵手要巧。有秧歌,就有快乐,插秧就是种乐趣。一丘田,一顿早饭的功夫基本上就栽满了,姑娘们栽上我家的,栽你家,栽好何三大爷家的,栽满大爷家。有耕作的地方就有秧歌,有劳作的地方就有快乐。
小满当晚,家乡人不约而同到嗮谷场,举行篝火晚会,庆祝满前时令栽上秧禾,期待金秋有好收成,谷满仓满。晚会准备妥当,长辈带领晚辈祈祷,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仪式结束,何三大爷拉起土琵琶,满大爷吹起老笛子,小伙们猜拳吃酒,姑娘们扭起秧歌。家乡的秧歌在宣威整个东北镇最有名气,十里八村的乡民都赶来捧场,小姑当年的秧歌扭得最好,被阿鲁村的秧歌王子看上,成就一段美好姻缘,可好景不长,小姑的丈夫患疾早逝,小姑从未改嫁,也不再扭秧歌。小姑说,秧歌只有他懂,他不在,我扭秧歌还有啥意义?
多年以后,家乡的田骤减,有的被征占,有的改为旱地,秧田几乎消失殆尽,曾经的秧歌不复存在。
何三大爷、满大爷、小姑的秧歌只是依稀在梦里出现,恍若隔世。
(作者单位: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区人民检察院)